{cat_music}1980437275{/cat_music}
现在是凌晨零点三十分,躺在床上听着这首歌,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 感到非常的亲切。
高考后的第五十八天,我想了想在小洲的日子。
离开小洲也快要半年了,那些画画的日子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让我怀念,反而是那些每日一个人坐在六楼的铁皮屋顶上吃盒饭的情景更能勾起我对小洲的回忆。六楼的一栋房子在广州真的说不上高,但是在市郊的小洲村却足够给你无限宽阔的视野。这是沛南租下来的好地方。无数的傍晚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无数轰隆隆的飞机融入雾气弥漫的城市的上空,看着黄昏橘色的夕阳沉入幕色,天边绚烂的云霞像是动漫里美丽影象,妖娆醉人!然后是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闪烁的霓虹灯把城市的夜空染成了暗红色,借鲁迅《秋夜》里说的,奇怪而高!看不到星星。这时候我常常在屋顶听的是班得瑞。
有时候沛南在外面回来见到门开着在房子里又找不到我,他就会知道,我肯定又是在屋顶发呆了。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样子的发呆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人总是得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让自己的思想随着无边的夜任意驰骋。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会在那些万籁寂静的时候茅塞顿开。但我知道很多时候我的确是过了,像戒不掉的瘾一样,一点一点噬食着年少如花的青春。呵,言,重了。
和我一起住的是一个复读生,叫黄沛南,来自汕头,一个日日夜夜吹着太平洋海风的海滨城市。他和我说,虽说是经济特区,但汕头这个城市现在是很不景气的,可能是以前太过依赖政策了,总以为国家会一直这样养着我们的样子,导致汕头没有发展出一些有实力的本地企业。其实也许也是因为规划的问题。我也没说什么,我常常对他说,我的家乡,有着延绵起伏的大山,有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起风时翻滚的稻浪,有清澈的小河与古老的泉水,有老去的村庄和祖上的祠堂……
他总是羡慕的说,你真幸福,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你那里游玩,或者到那里养老,嗯,至少要找这样一个地方。又像是自言自语,呵呵,我心里乐着。
有时候真的觉得沛南这个人可爱极了,有一个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乾总已经去北京了,我睡了他的下铺,而沛南就睡在上铺。乾总是谁?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乾总是另一个复读生,而且是复读第二年的,画画挺厉害的,但做人就有点那个……就是我们三个人租房子一起住的。那天晚上沛南像往常一样在接近凌晨的时候熄了灯想要睡觉,而我有睡前阅读的习惯便在下铺亮着小台灯继续看书。可能是因为刚过了12点,窗外有很吵杂的声音传来。原来是旁边那栋出租屋的楼顶上有学生在庆祝生日,那栋房子好像是五层,是租给某个画室当学生宿舍的,男女混住。那个画室叫什么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她们在五楼狂欢我们就在旁边的六楼睡觉,吵杂的声音传上来就在耳边。把玻璃窗拉上也没用。沛南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偶尔转过身看看窗外的下面是什么情况(床就贴着窗户),纠结得很。又转回来自言自语地说,神经病啊,这里是居民区啊,还让人睡么!烦死了,我得骂一骂她们。然后沛南拉开了窗把头伸出一点点,“喂……”,停住了,想了一会儿,把窗关上,转过身来装着睡觉的样子。然后似乎是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别人生日我这样骂别人不太好吧?”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钦佩他,沛南,你太伟大了。又过了一会,下面玩得越来越起劲,沛南实在忍不住,吵死人了,妈的,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不狠狠的骂他们一顿难以泄愤。然后他转过身去,拉开窗,头探出去,犹豫了一下子,然后压低声音似乎是哀求的说,朋友,你生日别弄得我们也不能睡哩。我狂晕,暗地里嗄嗄地笑。
下面忽然有人说,嘘……声音小一点,别人要睡觉呢,我们声音小一点。收敛了一会儿,沛南舒了一囗气,以为是可以休息了。可过了不久,下面又热闹了起来。沛南要崩溃了,喃着,不,我得想个办法!投诉?太慢了。扔东西?对,我得扔鞋东西。拉开了窗,犹豫了,你傻啊,伤了别人怎么办。但我得休息啊……沛南彼时那个纠结,我被沛南这样翻来覆去的折腾逗得彻底乐了。
“喂,小帅哥,好纠结啊,你说我应不应该扔东西,这群神经病吵死了”他知道我还没有睡。
我只是一直在笑。”等一下热闹过了应该就会静下来的了,再等等吧!”我合上书,过了不久下面就真的渐渐开始静下来了。
一点半了……
那个晚上我真的被他逗的开心极了。可能我的文字无法把当时的状态很好地描述出来,但是你肯定能感觉到我当时是真的快乐!
他常问我,为什么学画画啊?我说,考大学呗。 他说,学画画有什么用,付出的比别人都多,得到的知识又是那么狭窄,你以后回学校一定要好好珍惜学文化的机会。他说他去年有个美术老师哄着他学美术,并且当时他正和一个女生不和然后他就逃来广州学美术了。我想可能是恋爱不顺便逃了出来。他学画画的路也是够坎坷的。刚来广州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他说“我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个小孩,什么都不懂,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时候并不知道普通的小画室学费是多少,他竟然收了我三万,我也傻乎乎的照给。”他说他那时候真的还小,根本就不知道钱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父母给了,就花得理所当然。后来在广州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渐渐懂得了钱的好处,也知道了学费根本用不了那么昂贵,心有不甘。也因为那时候的他性格孤僻,不讨老师喜欢。学了好几个月之后,在准备面对高考的时候,他却被告知,他不能参加高考。因为他是理科生。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并没有对他说清楚理科生是不能报考艺术的。那时候的他彻底的傻了,那么没日没夜地辛苦了几个月,花了那么多的钱。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欺骗了他,让他付出了那么多最后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他心上过不去,颓废了。真的,我们怎么能够理解那种痛苦,为了高考付出的青春,就这样一场空!他到处游荡,不再去上课,对他来说,上课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偶尔会心血来潮,带着画板外出写生。他对我说,除了画画他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他已经万念俱灰了。
有一次他在湖边写生,一个女孩走过来夸他画得好看,他就对女孩说出了不能参加高考的经历。女孩说了很多鼓励他的话,还说,你还年轻!!
后来他决定复读,转学文科。没有参加过高考的复读生自然压力比谁都大。相对于应届生他有”复读”的压力,相对于其他复读生他有“没考试经验”的压力。但这一年的经历已经让他心智渐渐成熟,不再那么的冷漠孤僻棱角分明。
“你是程雨弦吗,乾总和我说了,说你想在宿舍搬出来住,是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画室门口画速写,沛南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说是的。“那你搬去我那里住吧,我明天回学校学文化课。你也好帮乾总分担一下房租。”就这样的认识了,可能是他觉得我像他的曾经,后来他就渐渐地对我讲述了上面的故事。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在哪看到了这样一个条规定,从2012年起,广东省所有的艺术生、体育生均不分文理……我告诉他,理科生也可以考艺术了。他无奈又悲催,人生总是那么的戏剧!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沛南跑完六楼的楼梯很累的回来,见我又是一个人在外面发呆。就对我说,走呗,跟我到外面逛逛。去哪?去找我弟,在大学城。广州大学城在珠江的一个小岛上,小洲村就在旁边,隔着一座大桥。
在广州美术学院与广东工业大学之间的一个公交站下了车,大学城里总是非常干净,安静的。之前的我总是在白天里一个人傻逛。却从来没有想过,大学城的夜是这么迷人的。公路上没有车,宽趟得奢侈的人行道或单车道上铺满了路灯洒下来的淡黄色,并染着道旁摇曳的树椪投下来的荒凉的影子,有着电影里关于青春的浪漫情调。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偶尔变换的红绿灯在数着一些毫无意义的阿拉伯数字,在寂静里耀武扬威。附近大部分的建筑若幻若现地隐藏在朦胧的夜色里,有的建筑却被月亮的光华切割出线条明确的轮廓,像极了我梦中的雨夜里闪电时刹那的光辉切割出的古堡的轮廓。
过了不久他弟一个人骑着单车在昏暗的路灯下缓缓向我们走来,慢慢撩动寂静的夜色。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画面,在这大学城美丽的夜色里。让我很容易联想到了“浪漫”这个词,但是它的迷人又不是随便一个浪漫就可以诠释的。他骑着单车越来越近,皮肤在夜里显得有点黝黑,和沛南一样有着略尖的下巴,眼神青涩而恍惚。来到面前停了车笑着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沛南打招呼。然后好像是在南亭逛了一圈,期间他俩用潮汕话聊天,偶尔用普通话和我搭讪一下,沛南还不太会说白话。我本来就不善于说话,沛南他弟也一样,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很内敛,却有着很明朗的笑容。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应该是九月低,他从汕头来广州读广东工业大学还不够一个月。沛南去银行取钱的时候我问推着单车的他,来这里读大学习惯吗?他怯怯地说,眼神涣散,“刚刚来的时候是不习惯,但久了就好了。”然后笑一笑,像个孩子。他又说,”这里南亭我已经来过很多次的了。你看,”他指着路边的一家烧烤店对我说,“那家店的烧烤很好吃的。”我顺着望去,因为南亭村到处都在改建,所以路是坑坑洼洼的。烧烤店就在路边,一辆车开过烟尘滚滚。店家还若无其事地翻着他的烤肉。
原来是他生病了,沛南来是为了带他去药店看病。然后他回学校停好单车,三个人坐车到了广州大学商业区。他话开始多了起来,主动地对我说,哪里是会展中心,哪里是科技厅,哪层是专卖女性内衣,哪里有网吧,哪里有KFC……显然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并为此自豪。像个孩子一样乐此不倦地对别人数着自己的见识并等待着别人的赞许,其实我想告诉他我不是第一次来的,但我没有,我能感觉得到他内心的这种简单的快乐。
要回去的时候,我和沛南回小洲村。沛南他弟回广东工业大学,在我们对面的公交站等车。后来沛南似乎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跑到马路对面,跟他弟说了些什么,又跑了回来。我对沛南说,要不要陪他回去然后我们再走?沛南说不用了,他自己的路总是要他自己走的!
“不如我们走路回去吧,别等车了,我们走吧!”沛南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别吓我。
“走路?用双腿?回小洲村?你没事吧?”
“怎样?不敢啊?”
”谁说不敢!我不知道路。”
“跟着我就行了。”
“有多远啊?”
“不远,走不断你的腿的!”
……
走着的时候沛南问我,“我弟是不是很幼稚啊?”
“没有,你怎么这样说啊!”
“其实一年前的我也和他一样的单纯,那时候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学习。来了广州之后,回去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在这里这些日子会逼着你成长,逼着你成熟!”
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恐惧,因为那时候的我一个人在广州也快有两个月了,我已经开始有那种压抑感,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那时候我常常看见你一个人在晚上下了课之后在画室门前画速写,在夜里显得格外的安静和孤单,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便叫你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也好照顾一下。我是看不惯凌桐把你带来这里又没有把你照看好。我每次看到你一个人在屋顶发呆的时候都会想起以前自己……”沛南这样说着。
我默默地听着。
“人总是要交际的,你不能一直都这样!”他对我说。
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但当时没有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因此便选择了不去表达。如果可以用文字来代替语言的话,有时候我真的宁愿做个哑巴。
走到高架桥底的时候,沛南对我说,我们到那边歇一下吧。我给你看个视频!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周哥制作的视频。是一些画画、生活和玩的照片做成的视频,是他们去年在上善画室的全部回忆。我看得难过,为什么他们有这么深刻的友情和回忆,而我们这一届来上善的人却没有这种荣幸。他们师生混在一起,洗菜、洗碗、烧烤……其乐无穷!我看到了照片上的龙哥、谭总、乾总、杨靖、凌桐、吕凌洁他们。我想这些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青春,一群人一起学一起玩,一起进步一起快乐。我想沛南是想要告诉我,人是应该活在群体当中的。
在视频的尾声我看到了一张沛南的照片,如果不是照片上有标名字我几乎是认不出他来。头发长长地的盖了额头,眼神冷得很。我竟不能想象一年时间会把他变成今天那样,成熟而稳重。
看完视频之后我们继续走。那晚两个人一起走了很久。走了很长很长的夜路……
我问他想考什么学校,他说要考广州美术学院。他弟就在旁边的广东工业大学。
过了北亭村、北亭广场,过大桥的时候停了下来歇会儿。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大桥微微颤动。夜空零散地挂着几颗星。在广州你是很难看到星星的。珠江水倒影的霓虹城荡漾在夜幕下、渔船暗绿的灯光渐渐远去。月色渐次明朗……
沛南打电话给凌桐,叫我听。凌桐在电话里问我,“有没有和哪个老师熟络起来?”
“问这干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
“我就是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才问,你看如果你是刘巧政这样的人跟谁都有话说,我就用不着操这个心了……”
后面说了什么我已记不起来,那时候的凌桐已经回复读学校补习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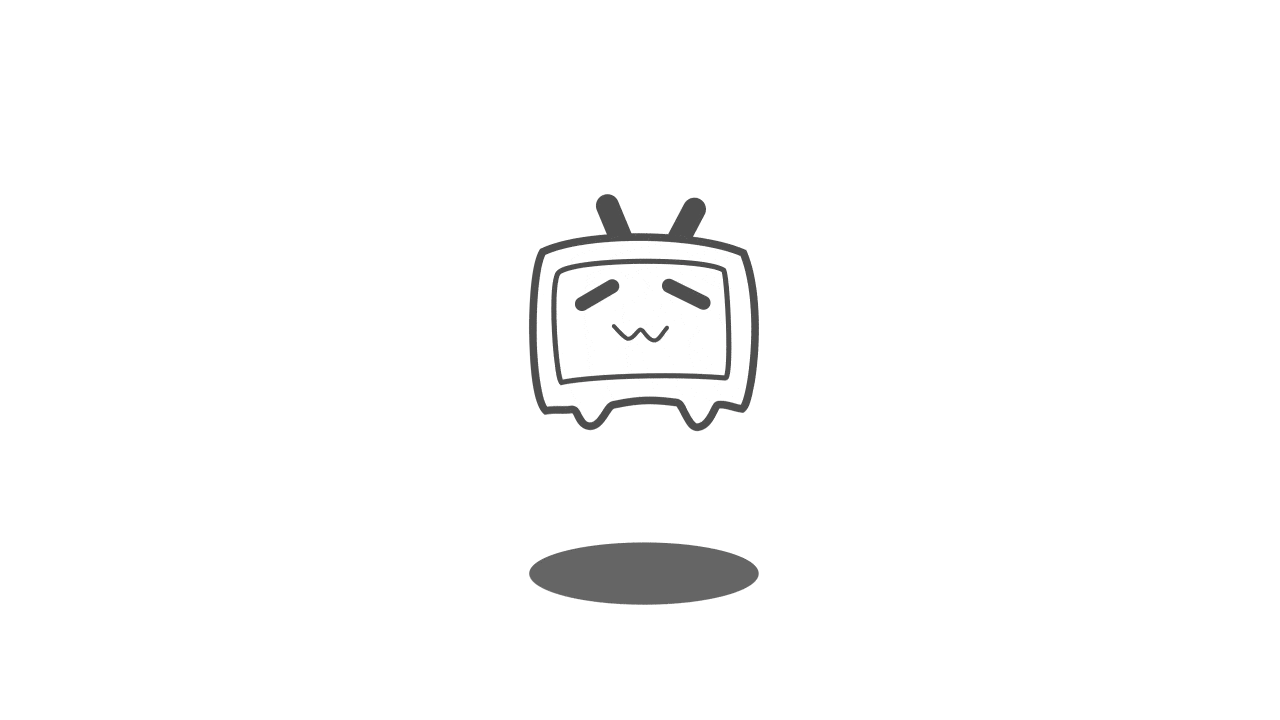
参与讨论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参与讨论
没有发现评论
暂无评论